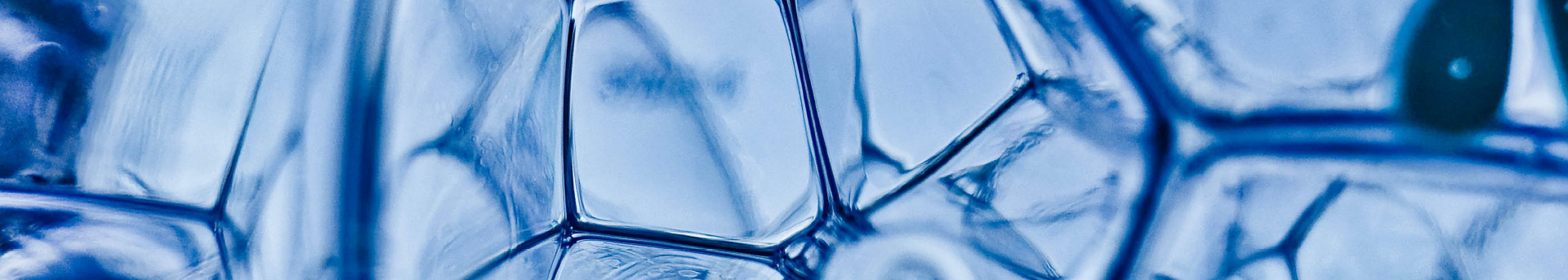

引言
商业秘密作为重要的无形资产,是企业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保障。然而,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和技术的迅速迭代,有关商业秘密的纠纷层出不穷。在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反向工程抗辩是被诉侵权人常用的抗辩理由之一。
反向工程,是指通过技术手段对从公开渠道取得的产品进行拆卸、测绘、分析等而获得该产品的有关技术信息。在很多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被告常常辩称其并未非法获取或使用原告的商业秘密,而是通过正当的反向工程手段从公开的或合法获得的产品中获得了技术信息,从而主张并不构成商业秘密侵权。
面对这一抗辩,许多企业常常会困惑:“如果他人通过正当的手段成功破解了公司的技术秘密,那么是否意味着技术秘密可以被随意实施?”实际上,反向工程抗辩需要遵循相应的适用条件,并非所有的反向工程抗辩均会获得法院支持,尤其,在可能存在故意侵权的情形下,为了充分保护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法院会从严审理反向工程抗辩。
本文将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判例,详细探讨反向工程抗辩在商业秘密纠纷中的适用问题,并分析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的考虑因素,为企业如何更有效地保护自身的商业秘密提供实践指导和法律建议。
一、反向工程的对象和相应技术信息是否从公开渠道合法获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2款及第3款规定:“前款所称的反向工程,是指通过技术手段对从公开渠道取得的产品进行拆卸、测绘、分析等而获得该产品的有关技术信息。
被诉侵权人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后,又以反向工程为由主张未侵犯商业秘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一)以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电子侵入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上述法律规定在法院实务审判中也得以体现,在(2022)最高法知民终2278号侵害商业秘密案的二审判决[1]中,记载了一审法院适用上述法律作出的论述:“原审被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被实施反向工程的图纸或产品系其从公开渠道合法取得,亦不能就拆卸、测绘、分析等过程进行充分举证并且作出合理说明。故原审被告反向工程的抗辩主张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亦不符合情理,不予采信。”最高人民法院最终驳回上诉,维持了一审法院的认定。
在(2013)苏知民终字第159号侵害商业秘密案的二审判决[2]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关于原审被告主张导流铜棒的技术信息系通过反向工程获得问题。反向工程是指通过技术手段对从公开渠道取得的产品进行拆卸、测绘、分析等而获得该产品的有关技术信息。本案中,如前文所述,没有证据显示原审被告从公开渠道购买到了原审原告的甩带轮整体设备,亦无其进行反向工程获得涉案技术信息的任何证据,故对其该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结合法律规定及上述案例可知:被实施反向工程的对象须为公开渠道取得的产品,且技术信息须为对产品通过拆卸、测绘、分析等合法手段取得,如果以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电子侵入等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的,其反向工程的主张无法成立。
二、反向工程实施主体是否对相关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3款:“被诉侵权人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后,又以反向工程为由主张未侵犯商业秘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可以包括以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电子侵入等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侵权人是通过正当手段获取了商业秘密。例如,侵权人是权利人(如原单位)的前员工,在原单位就职期间因正常的工作需要获取了商业秘密,但离职后向新单位披露、继续使用并允许新单位使用原单位的商业秘密;或者,侵权人是权利人的合作方,因合作需要或履行合同义务获取了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但违反保密义务向第三人披露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或者超出合同授权范围披露、使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这种情况下,前员工或合作方对权利人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如果其提出反向工程抗辩,则很难得到法院支持。
在(2014)浙知终字第60号侵害商业秘密案的二审判决[3]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上述规定,被实施反向工程的产品应当是从公开渠道取得的产品,且反向工程的实施人不能是对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如果是以不正当手段知悉了他人商业秘密之后又以反向工程为由主张获取行为合法的,该抗辩主张不能成立。三原审被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被实施反向工程的产品系其从公开渠道合法取得的原告的产品,而原审被告三作为实施人本身负有不得将原告技术图纸泄露、保守原告商业秘密等义务,且三原审被告亦不能就拆卸、测绘、分析等过程进行充分举证并且作出合理说明。相反,鉴定过程中对双方当事人提供的技术图纸进行比对……上述反向工程抗辩主张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亦不符合情理,该院不予采信。”
三、反向工程是否实际实施
在(2016)鲁民终1364号侵害商业秘密案二审判决书[4]中,原审法院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审被告应对‘反向工程’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提供其‘反向工程’的证据。原审被告未能提交其主张的通过拆解同类产品获取相关技术信息的实际测绘、分析所获的技术数据……故其‘反向工程’的抗辩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同样地,在二审判决中,二审法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也认定“原审被告不能举证证明该产品系其独立研发或通过‘反向工程’获得”。
在(2007)粤高法民三终字第322号侵害商业秘密案二审判决书[5]中,原审被告主张其生产产品所使用的图纸均为其根据现行公开的资料参考市场上正常销售的相关产品自行绘制而来,并提交了相关图纸。但二审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审被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曾经向市场购买了相关产品并通过拆卸、测绘、分析等获得了该产品的有关技术信息,而且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其自行绘制的时间、开发研制人、绘图人等重要事实。因此,原审被告的举证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在(2001)浙经二终字第102号侵害商业秘密案二审判决书[6]中,原审被告在二审中提交了其与第三方公司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第三方公司及其员工出具的证明、原审被告支付技术服务费的发票、原审被告用以测绘的样机的照片及购买样机的发票,以证明其系通过反向工程方法获得部分图纸。最终,二审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原审被告所举证据能相互印证证明反向工程成立[7]。
由上述案例可知,被控侵权人以反向工程作为抗辩理由的,需要提供实际实施反向工程的证据材料,例如,通过技术手段对产品进行拆卸、测绘、分析的实验记录、照片、发票、合同、测绘报告、分析报告、周报、技术底稿等材料。一般情况下,尺寸、外观、化学成分等可以通过反向工程获得,而详细尺寸(例如公差)、工艺流程、步骤、合成条件及材料的特殊处理方式等则不易获得,对被控侵权人的证明要求也会更高;尤其是,有些技术参数往往需要借助专业的实验平台才能开展反向工程,也需要考察被控侵权人是否具备实施反向工程的客观条件。
四、通过实际实施的反向工程获得的技术秘密是否与涉案商业秘密一致
在(2023)最高法知民终1590号侵害商业秘密案二审判决书[8]中,原审被告威马公司主张权利人吉利公司涉案12套图纸及数模所承载的技术信息被现有技术公开,底盘零部件的结构、连接关系及基本尺寸在相关车辆上市销售后通过拆解、反向工程等即可获得,因此不具有非公知性。二审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涉案新能源汽车底盘应用技术以及其中的12套图纸及数模所承载的技术信息包括底盘零部件的形状、结构、尺寸、尺寸公差、形位公差、表面粗糙度、技术要求、关键尺寸精度、材料信息、工艺信息、性能要求、细节要求等具体信息,是一套具体、完整、可用于新能源汽车底盘制造的技术信息。即便在吉某方使用涉案技术秘密的相关型号车辆上市销售后,通过购买车辆进行拆解并利用激光扫描等方式实施反向工程,亦仅能获得有关底盘零部件结构、连接关系以及基本尺寸等个别简单技术信息,难以获得数模中有关产品尺寸的精准数据以及数模中有关产品内部结构的技术信息。至于底盘零部件图纸中的其他技术信息,如尺寸公差、形位公差、表面粗糙度、技术要求、材料信息、工艺信息、性能要求、细节要求等,即便通过反向工程方式亦难以准确获得……通过反向工程可以获得部分特定信息并不能证明涉案图纸及数模所承载的全部技术信息均不具有非公知性”。
在(2014)浙知终字第60号侵害商业秘密案二审判决书[9]中,原审被告主张其在对权利人产品进行维修和翻新的过程中通过反向工程方式获得相关技术秘密,二审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出,“鉴定报告可以证明‘连杆冷却系统’和‘锁模装置’的设置是多解的,不同的设计人员设计方式不一样,相关的工艺参数等技术信息也不相同……原审被告不能证明其通过反向工程获取了上述技术信息”。
由上述案例可知,被控侵权人以反向工程作为抗辩理由的,需要证明通过实际实施的反向工程获得的技术秘密与涉案商业秘密一致。一般情况下,权利人通常会明确指出其技术秘密的载体以及具体主张的秘点。若通过反向工程所获得的技术信息与涉案技术秘密一致,则反向工程抗辩成立;反之,若存在实质性区别或仅获得部分特定信息,则反向工程抗辩不成立。
五、权利人是否采取有效的技术措施防止他人进行反向工程
在(2020)最高法知民终538号侵害商业秘密案[10]中,原审原告认为原审被告在另案证据保全时拆解了原审原告在市场中公开销售产品,获得了原审原告的技术秘密,然而,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鉴于涉案技术秘密载体为市场流通产品,属于外部性载体,故原审原告为实现保密目的所采取的保密措施,应能对抗不特定第三人通过反向工程获取其技术秘密……通过拆解GTR-7001气体透过率测试仪,可直接观察到秘密点2、3、4、5,同时,本领域技术人员‘通过常理’可知晓秘密点1和6……原审原告在其GTR-7001气体透过率测试仪上贴附的标签,从其载明的文字内容来看属于安全性提示以及产品维修担保提示,故不构成以保密为目的的保密措施”。最终,最高人民法院认定原审原告主张保护的涉案技术秘密因缺乏“相应保密措施”而不能成立。
上述案例即是权利人未采取技术措施防止他人进行反向工程而导致原告败诉的一个例证。相反,如果权利人采取了有效的技术措施,如“采取物理上的保密措施,以对抗他人的反向工程,如采取一体化结构,拆解将破坏技术秘密等”[11],被告的反向工程抗辩可能会被认定为不成立。另外,如果“技术秘密本身的性质,使得他人即使拆解了载有技术秘密的产品,亦无法通过分析获知该技术秘密”[12],那么被告的反向工程抗辩也被认定为不成立。
需要注意的是,防止他人进行反向工程的措施必须是物理上的技术措施,而非普通的保密措施。即使贴附在产品上的标签所载明的文字内容以保密为目的,如“内含商业秘密,严禁撕毁”等,此时该标签仍不能构成可以对抗他人反向工程的物理保密措施,被告的反向工程抗辩仍然可能成立。
结语
回到本文开篇的问题:“如果他人通过正当的手段成功破解了公司的技术秘密,那么是否意味着技术秘密可以被随意实施?”通过分析上述案例我们可以知道,答案是否定的。反向工程抗辩是否成立,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反向工程的对象和相应技术信息是否从公开渠道合法获得、实施主体是否承担保密义务、反向工程是否实际实施以及是否取得了与涉案商业秘密相同的技术秘密等。此外,权利人是否采取有效的技术措施防止他人进行反向工程,也是法院判断的重要依据。
通过本文的案例和分析也可以总结出企业在日常经营中应当注意的要点。首先,企业应在产品上市前进行反向工程测试,评估其技术秘密可能被破解的风险。这一过程有助于识别技术中可能被外部分析、拆解并复制的环节,从而提前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其次,对于不同性质的技术,应采取差异化的保护策略。例如,对于难以通过分析获知的技术秘密,可依靠其本身性质进行保护;而对于可以通过拆解获取的技术,则需采取物理上的技术措施,阻止他人进行反向工程。
企业在面临日益复杂的商业秘密保护挑战时,需要从源头上加强技术防护,提升内部管理和法律合规意识。通过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不仅可以降低因商业秘密被破解带来的风险,还能够在商业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确保企业的创新成果得到应有的保护。
[6] (2001)浙经二终字第102号二审民事判决书
[7] 兰国红.知产北京.你知道反向工程吗?它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的有效抗辩吗?|法护创新进行时·法官小课堂[EB/OL].[20230718]. https://mp.weixin.qq.com/s/Mg6G5ezXLfzGBtVtm17taQ
[8] (2023)最高法知民终1590号二审判决书
[9] 同注3
[10] (2020)最高法知民终538号二审民事判决书
[11] 同注10
[12] 同注10
京ICP备05019364号-1 ![]() 京公网安备110105011258
京公网安备110105011258
近日,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本所”)发现,网络上存在将一家名为“广州海问睿律咨询顾问有限公司”的主体与本所进行不当关联的大量不实信息,导致社会公众产生混淆与误解,也对本所的声誉及正常执业活动造成不良影响。
本所特此澄清,本所与“广州海问睿律咨询顾问有限公司”(成立于2025年11月)不存在任何隶属、投资、关联、合作、授权或品牌许可关系,亦从未授权任何主体以“海问”的名义提供法律咨询服务,该公司的任何行为与本所无关。更多详情,请点击左下方按钮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