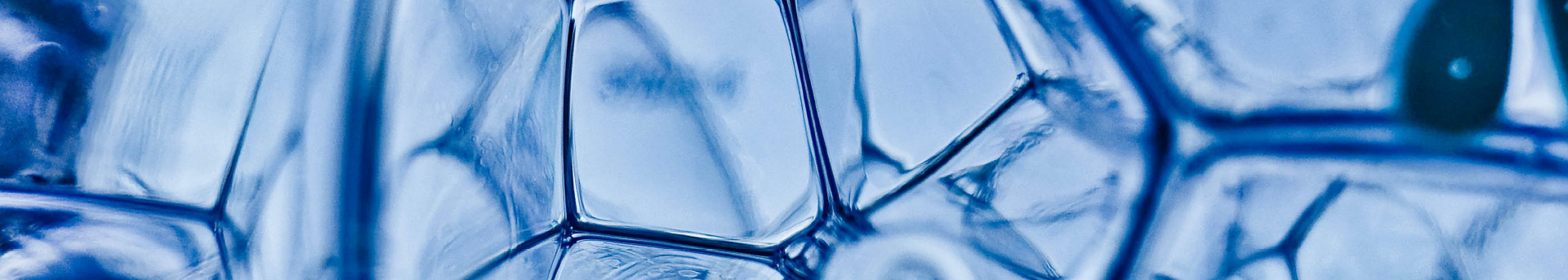

在《外商投资数字化业务拓界:外资增值电信业务进一步开放(上)》中,我们对工业和信息化部(简称“工信部”)颁布的《增值电信业务扩大对外开放试点方案》及其配套规定开启的本次外商投资增值电信业务试点(简称“本次试点”或“新规”)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对本次试点的开放类别、开放地域、申请流程、第一批试点13家批复企业的情况进行了分析。
在本次试点背景下,外资全资持股的境内公司,可以申请相应的增值电信业务牌照试点批复,这给一些自身业务形态涉及增值电信业务的跨国企业(简称“产业型外资企业”)在华拓展业务赋予了更大的空间,也要求投资人投资到从事增值电信业务活动的目标公司的项目时,具备更高的结构设计判断能力,还给境外资本市场运作活动中的结构设计、增值电信业务资质必要性论证提出了更精细化的分析要求。本文介绍以上项目执行过程中的相关问题,结合本次试点的规定,分析新规带来的新关注点。
1、新规对日常业务项目的影响:或开启业务布局全链路自控时代
此前,一些境外数据中心业务经营者在中国进行布局的过程中,具有实际在中国境内开展IaaS、PaaS等基础云服务的需求。
本次试点开展之前,以B11类“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Internet Data Center,简称“IDC”)为代表的泛IDC业务没有一般性地向外资企业开放,使得此类境外数据中心业务经营者仅能以合作的方式在中国开展软件服务业务。例如,亚马逊云与光环新网合作,由光环新网提供IDC服务,亚马逊向光环新网提供技术支持和专业指导;微软与世纪互联进行合作,世纪互联提供IDC服务。
本次试点开启之后,境外经营者(而非此前限于港澳经营者)可以全资持股境内实体,并使用该境内实体申请B11类业务的资质试点批复。如果成功获批,外商全资的境内企业可以直接经营该类业务,不需要寻找境内IDC证持牌主体进行合作,不需要特别通过“境内合作方提供IDC服务+外资企业提供软件与技术”的中外合作模式完成服务闭环。
其中,特别考虑到,在2016年IDC证的电信监管政策更新前,部分境外经营者曾经直接或以类似直接的方式经营数据中心业务,例如,IDC服务由境外经营者在中国的主体提供,业务合同是由境外经营者在中国的主体直接签署。但是,在2016年初IDC证电信监管政策更新后,境外经营者的业务经营方式基于合规要求而有较为实质性的调整,例如,根据亚马逊中国的公告信息,自2016年8月1日起,亚马逊云服务(中国)北京区域的服务将由光环新网运营和提供……在新的运营模式下,光环新网将与客户签署合同,提供账单和发票。因此,在本次试点推开的情况下,境外经营者有相对充分的动力和“刚需”,重新对相关业务进行直接把控和经营。
值得注意的是,如我们在《外商投资数字化业务拓界:外资增值电信业务进一步开放(上)》所提及,IDC业务资质,以城市为单位进行机房申请和测评,通过测评的城市,会写入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但是,本次试点又仅在北京、上海、深圳、海南的试点区域进行,并且要求经营主体注册地、服务设施(含租用、购买等设施)放置地须在同一试点区域内,不得购买、租用本试点区域外CDN等设施开展加速服务。例如,一个外商投资企业在北京市获得试点,经营IDC业务,则IDC业务有关的服务器、机房等应当在北京市内,且该企业不能租用北京以外的CDN服务进行加速。因此,本次试点的政策,暂适用于在相对特定区域内部署服务器(机房)、辐射周边用户的云服务供应商,特别对于IaaS形态的服务提供者而言,尤其应考虑这一政策要求,其无法通过“一地获批试点+多地部署机房”的方式拓展服务范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次已经获得试点批复的13家企业当中,暂时没有企业获得B11类(即IDC)业务许可。在新规的后续执行过程当中,值得观望是否有提供数据中心业务为主的产业型外资企业获得此类试点批复。
2、投资与资本市场项目:挥别“轻重分离”和“一套控制合同解决一切”
a. 布局在试点区域的IDC项目有望告别“轻重分离”结构
在一部分项目中,外资企业为了实现在中国境内投资数据中心业务的目的,可能会在项目中采用“轻重分离”的结构。
该结构的含义是,一方面,将数据中心业务当中最“重”的部分——不动产、机房和部分供电、供网、散热、安保基础设施——由外资企业在中国设立的独资企业持有。另一方面,由中国籍人士设立一家纯内资企业,持有数据中心业务所需要的主要知识产权(例如系统、软件、技术支持能力等)、相应的机柜甚至服务器等资产,并据此由内资企业来申请B11类等增值电信资质。获得资质后,由内资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达成一系列业务合作,实际上形成共同合作对外提供数据中心业务的模式。
在这一结构中,相对较“重”的资产,也就是不动产和部分基础设施,由外资企业持有。相对“轻”的部分,例如知识产权(系统、软件、技术支持能力等)和增值电信牌照由内资企业持有,形成业务经营资源上的“轻重分离”。
上述结构本身也存在一定问题,例如,一方面,毕竟资产并不统一由一个实体全部拥有,而是需要在不同实体之间建立一系列商业安排与协议,所以,外资企业本身并未对持有知识产权和增值电信牌照的内资企业进行直接的股权控制,在控制力度上有所减弱;另一方面,内资企业由于是持有牌照的主体,所以大部分的业务合同需要由内资企业来签署,内资企业再通过与外资企业就其所持有的重资产部分进行业务合作并向外资企业支付技术服务费等方式,将一部分收入支付给持有重资产的外资企业,但在这一过程中,难免有额外的费用成本和税务损耗。
在本次试点中,如果外资企业可以通过在一个试点地区获得批复来覆盖其客户群体,那么可能可以适当考虑是否采用直接持股方式,直接在某一个试点城市当地申请获得IDC业务的试点批复,直接经营数据中心业务。一方面可以解决上文提到的控制力不够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不同主体之间支付服务费带来的额外费用成本和税务耗损。
b. 投资和资本市场项目中对所需电信资质的更精细评估
就目标公司(投资项目中的被投主体,或资本市场项目中的发行人)是否需要取得某些类别的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而言,目标公司的业务如果涉及到线上要素(不论是主营业务就是线上的互联网平台业务,还是主营业务伴随有商城、用户论坛等线上属性的服务),则其业务就可能与一些增值电信牌照的业务形态相关,或者趋于类似。
例如,就SaaS服务而言,纯粹的自营SaaS,功能可能包括一些自营增值业务(例如办公软件、效率软件、甚至接入大模型能力处理企业客户的用户销售线索或者企业客户的企业文档等)向订阅SaaS服务的用户收取费用,但一些企业同时也提供用户与用户之间的聊天、类论坛服务,有时带有信息消息资讯的推送服务,而推送服务当中又甚至进一步区分为目标公司自创资讯和增值信息的提供和第三方信息消息的推送等。这些不同业务形态叠加在一起,可能导致目标公司采取简化的业务资质判断策略,直接申请所有可能相关的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以图“一劳永逸”和“饱和式覆盖”,甚至抱有“以备不时之需”的心态。其中,尤其以B25类“信息服务业务”(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简称“ICP”)证这一资质类别为典型。原因是这一牌照涉及的业务范围涵盖各类“信息服务业务”,和相当大数量的、涉及线上业务的目标公司业务形态有些相似。
但是,ICP证此前一直都存在外资比例不高于50%的限制。虽然在此前实践当中,外资达到50%或以上申请人的ICP证申请流程,相较前几年而言已经有相对实质的程序精简和难度降低,但是毕竟仍然需要经历申请流程,而且是向工信部提交申请,所以整个程序依旧显得繁琐、耗精力,并且对于申请人而言,是否能够最终取得ICP证,可能依旧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基于前述种种因素的考虑,过往,有一些企业在融资过程中,特别是搭建红筹结构、在海外进行融资的过程中,可能倾向于直接搭建VIE(通过协议控制的可变利益实体)架构。采取VIE架构的主要原因,有如下两点:一方面,可以直接将境内持有增值电信业务牌照的内资企业“纳入”集团公司范围内;另一方面,可以避免非VIE的纯粹股权红筹架构(简称“股权红筹架构”)中可能涉及的“两步走”操作,即企业不需要专门为将设立在境内的内资企业纳入到集团公司境外架构体系内之目的,先由该境内内资企业引入小股比的外资非关联投资人,而后再由外商独资企业完成对该境内内资企业的收购。
上述倾向于直接采用VIE架构的设计思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其中,在2023年初,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境外上市备案管理办法正式出台生效之前,境外上市项目不需要取得中国证监会备案。所以,发行人是否采用VIE架构,对境外上市流程一般影响不实质。特别是对于美股上市项目而言,以发行人披露为主,并不严格考量VIE架构设立的必要性;港股项目则基于“narrowly tailored”原则的基本要求,需要发行人及境内律师结合当地监管法律法规及实践监管的要求,对VIE架构使用的业务范围和具体股比搭配的必要性进行论证,但基于市面上相对成熟的论证和应对思路,在符合该原则要求的情况下,实践中一般也不会实质延长境外证券监管机构和境外证券交易所对上市申请的审核时间。
但是,在2023年初中国证监会境外上市备案管理办法发布之后,境外上市需要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在进入中国证监会的备案流程时,如发行人带有VIE架构,在实践中,则可能实质影响、延长发行人通过备案的时间。这一因素也影响到上市前股权投资及投后管理阶段中,投资人对于目标公司股权架构现状及调整方案的评估思路,并且影响到目标公司(作为发行人)在境外资本市场上市筹备过程中的路径选择。从路线设计策略角度,为尽可能减轻目标公司未来上市申报在政府监管程序方面的不确定性,如果并非必须使用VIE架构,则目标公司(发行人)可能,且目标公司的股东也可能,倾向于尽量避免目标公司(发行人)采用VIE架构。
仅就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角度而言,如果目标公司业务形态确实不需要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或者业务形态涉及的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可以由外商独资企业持有,则目标公司不需要使用VIE架构,而可以采用股权红筹架构。例如,以企业服务SaaS业务为例,如果目标公司仅向企业用户提供公司自营的增值业务(例如办公软件、效率软件、接入大模型能力进行信息和文档的总结或修改等)并向用户收取费用,该形态可能不需要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所以,仅涉及该形态的目标公司(发行人)可以考虑采取股权红筹架构,不搭建VIE架构。如果发行人涉及典型的线上电商平台业务,则需要B21类“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尤其指其中的“交易处理业务”(经营性电子商务)类业务)的增值电信许可,该类许可近年来已经在全国开放外资股比限制,所以发行人可以考虑使用股权红筹架构,利用集团公司现有架构中的外商独资企业或者其子公司申请该类业务的增值电信许可。
c. 本次试点若干要素的不确定性和展望
本次试点是对外资突破50%股比获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的重要利好。在目标公司、投资人等各方在投资和资本市场项目下的选择路径规划时,一方面,需充分分析论证,依托本次试点的政策红利窗口,在需要的情况下尝试申请新的批复;另一方面,也需要关注本次试点的若干要素依旧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
● 试点效应:目前,第一批试点批复的13家机构已经公开。这批机构作为本次试点的第一批获得批复的主体,对于未来推进和铺开试点,具有重要示范意义。目标公司在评估及筹备自身的试点批复申请的过程中,也需要考虑第一批13家机构可能具有的试点效应,综合衡量目标公司后续自身获得批复的时间需求,以及获得批复情况下的具体使用场景(例如依托于具体项目,还是希望在融资或资本市场运作中补齐短板),合理规划申请策略和申请时点。
● 产业型外资企业背景:第一批试点批复的13家机构当中的大部分都具有跨国公司背景或产业经营者背景。这也符合本次试点真正的开放目的。目标公司在筹划自身申请策略时,可能需充分考虑上述因素可能存在的潜在政策导向。
● 部分类别牌照批复先例的暂时缺失:目前第一批试点批复的13家机构中,暂不涵盖取得IDC业务(即B11类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许可的主体。这一业务类别是此前业界最期待开放外资限制的业务类别之一。当然,这可能也是由于目前第一批试点批复机构的总数并不太多、样本有限等原因所导致。值得关注在后续批次的试点批复企业中,出现多大比重的IDC持证主体。
京ICP备05019364号-1 ![]() 京公网安备110105011258
京公网安备110105011258
近日,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本所”)发现,网络上存在将一家名为“广州海问睿律咨询顾问有限公司”的主体与本所进行不当关联的大量不实信息,导致社会公众产生混淆与误解,也对本所的声誉及正常执业活动造成不良影响。
本所特此澄清,本所与“广州海问睿律咨询顾问有限公司”(成立于2025年11月)不存在任何隶属、投资、关联、合作、授权或品牌许可关系,亦从未授权任何主体以“海问”的名义提供法律咨询服务,该公司的任何行为与本所无关。更多详情,请点击左下方按钮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