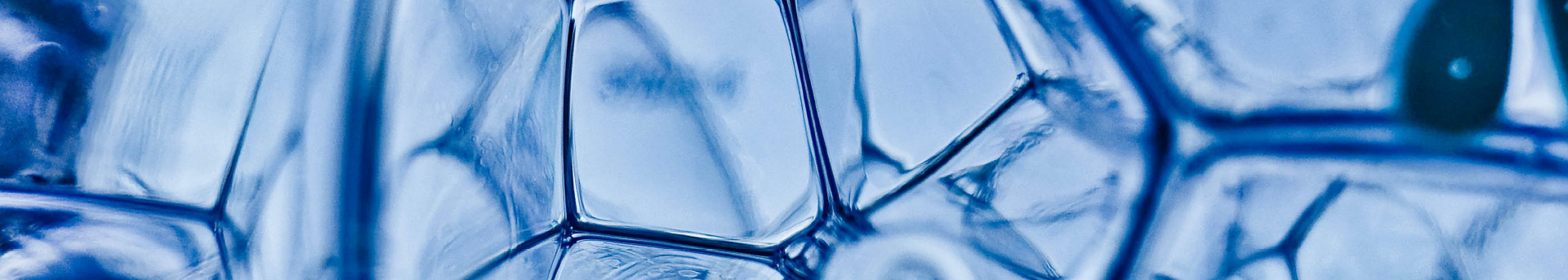

众所周知,诉讼活动中最重要的就是证据,常言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最关键也最不可缺少的取证环节就是侵权证据的固定与收集。在取证阶段,为避免打草惊蛇及取证现场不必要的冲突,权利人往往直接或通过委托的律师或调查公司等代理人以普通消费者的名义与侵权方进行接洽以取得侵权产品、宣传材料、场所照片等证据,并通常由公证处对相关取证过程以及取证结果进行公证,以确保取证的效力。因为在取证过程中,取证人以及公证人员均不会亮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因此该种取证方式也被称为“陷阱取证”。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陷阱取证”的效力常常引起争议,再加上公证程序规则对公证员有“亮明身份”的要求,有关知识产权侵权诉讼的相关规定又未明确对“商标侵权诉讼”中能否“匿名取证”做出特别规定,权利人在请求公证处配合对侵害商标权的行为进行公证取证时,总是需要对取证方式等问题进行特别沟通。
2020年1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知识产权证据规则》”),并于2020年11月18日施行。其中,第七条对“陷阱取证”的问题进行了规定。对于知识产权诉讼律师来说,该规定的具体适用,包括举证责任的负担、证据效力的采信等对于未来的取证、证据认定以及损害赔偿均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陷阱取证”的立法与司法回顾
“陷阱取证”最大的争议在于取证时未表明真实身份,以该种方式取得的证据效力如何认定。经过对规范性文件的梳理,在《知识产权证据规则》实施之前,关于“取证”有如下的内容:

《批复》中的相关规定会使得“未取得对方同意”而获得的录音证据效力存疑,也一度引发了公证员对于侵权取证公证过程中是否需要亮明身份的讨论与担忧,但是此后《民事证据规定》、《民诉法解释》、《著作权司法解释》等相关规定明确了相应侵权取证的效力。即侵权取证并无需亮明身份,某一证据能否被采信,判断标准在于相关证据的取得是否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是否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是否以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
在(2015)民提字第212号民事再审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对民事诉讼的取证效力进行了论述。在该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基于2002年4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规定,认定“法复[1995]2号批复所指的‘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应当理解为系对涉及对方当事人的隐私场所进行的偷录并侵犯对方当事人或其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六条关于‘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规定明确了该司法精神。本案中,张文武与陈志雄的谈话系在宾馆大厅的公共场所进行,录音系在该公共场所录制,除张文武的女儿外也未有其他人在场,并未侵犯任何人的合法权益,故对该录音证据应予采纳,并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即,未取得对方同意的录音证据能否作为证据采信的关键在于是否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是否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而非形式上“是否取得对方同意”。
在知识产权领域,最高人民法院在十五年前的公报案例已经对“陷阱取证”的证据效力进行了明确认定。在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红楼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与北京高术天力科技有限公司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中,历经一审、二审及再审程序。在一审程序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可了原告以普通消费者购买侵权产品的取证效力。在二审程序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不认可取证效力。争议的焦点即在于取证方式是否具有合法性。再审程序中,最高人民法院一锤定音,认定“对于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行为,主要根据该行为实质上的正当性进行判断。就本案而言,北大方正公司通过公证取证方式,不仅取得了高术天力公司现场安装盗版方正软件的证据,而且获取了其向其他客户销售盗版软件,实施同类侵权行为的证据和证据线索,其目的并无不正当性,其行为并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加之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行为具有隐蔽性较强、取证难度大等特点,采取该取证方式,有利于解决此类案件取证难问题,起到威慑和遏制侵权行为的作用,也符合依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精神”。
可以说,在大量的侵害知识产权纠纷中,只要满足证据的基本要求,权利人自己或者委托他人以普通消费者名义进行购买、磋商等证据的效力一般都会得到法院的采信。
二、从体系以及历史的角度理解“七条”
既然以往的司法实践已经对“陷阱取证”的效力达成了共识,那为什么《知识产权证据规则》还要专门对该种类型的证据专门进行规定呢?
笔者认为目的有二:一是该规定系对以往司法实践的总结,以往在知识产权三大领域中(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只有著作权领域有过专门的规定。本次的新规定,可以在立法层面明确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取证的统一适用。第二个目的,其实在于区分不同的取证方式所形成的证据的效力问题。
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第七条规定了两款,第一款规定的是“权利人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进行的取证,第二款规定的是“被诉侵权人基于他人行为而实施侵害知识产权行为所形成的证据”。本条出现了三个名词“权利人”、“他人”、“被诉侵权人”。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在前后两款中,“他人”的具体含义是不同的,否则将会产生非常荒谬的结果。即人为区分权利人自己以及权利人委托的他人取证的效力,显然与逻辑、常识不符。另外可以确定的是,该两款所规范的内容是不同的,否则将会造成法律规范的冗余。基于以上两点的分析,第一款中的“他人”应被解释为权利人的委托人,与权利人一起可以共同理解为权利人。而第二款中的“他人”,是指被控侵权人以外的“他人”,既包括权利人及其委托人,也包括与权利人有关联或无关联的第三方。
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第七条规定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取证。第一款所规定的侵权取证目的是“发现或者证明侵权行为”,即相关侵权行为一直存在,相关取证只是为了固定事实而已。第二款则规定的是例外情形,相比于第一条,该条有其他共同侵权主体的参与,即“他人”。按照学界的划分观点,第一条所针对的是“机会提供型”的侵权取证行为,即侵权人一直存在侵权行为,权利人取证只不过是为侵权方提供交易机会,符合正常商业逻辑。而第二种针对的是犯意形成型的侵权取证,即被控侵权人原本未从事相关侵权行为,而由于权利人或者第三人的诱导,导致被控侵权人实施了被控侵权行为。换言之,被控侵权人的“侵权行为”不仅偶发,甚至是直接由于“第三人”乃至“权利人”而发生。相比于前一种侵权行为,第二种侵权行为对权利人的损害要小很多。
为了验证上述理解,我们可以进一步对比《<知识产权证据规则>征求意见稿》与《知识产权证据规则》的文本,明显可以看出《<知识产权证据规则>征求意见稿》的规定更为清晰,可以印证上述判断,

《知识产权证据规则》区分不同的取证行为,原因在于第二款所规定的情形中,存在“他人”,即权利人以及被控侵权人以外的“第三方”。如果是权利人以外的第三方诱导侵权人侵权,那么权利人起诉后,侵权方可以再向第三方追责或者在诉讼中请求将第三方追加为共同被告应诉,要求第三方共同承担责任,有助于查清事实,公平分担责任。但是如果由于权利人自己诱导“侵权人”实施侵权行为,那么权利人不仅在“道义”上可责,侵权人亦难以再行“追责”,会对“被控侵权人”造成不公平。这也是《知识产权证据规则》第七条第二款特别规定了“他人取证”与“权利人取证”证据效力差别的根本原因。
《知识产权证据规则》之所以删除征求意见稿中“侵权故意”的表述,原因在于侵害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成立并不需要“侵权故意”这一构成要件,如果保留相关表述可能引起歧义。
在近期的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度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之一克诺尔·伯莱姆斯股份公司与衡水永信制动材料有限公司、衡水永泽制动材料有限公司、克诺尔制动系统有限公司、亚东实业(国际)有限公司、北京辉门进出口有限公司、赵树亮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中即涉及商标侵权陷阱取证的效力问题。在该案一审诉讼中,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代理人主动找到被告赵树亮,要求为其生产带有涉案商标标志的刹车片产品,甚至将原告产品及外包装的照片发给被告赵树亮,要求其提供与照片相同的产品。虽然被告永信公司生产了侵权产品及包装箱,但由于被告赵树亮是在原告代理人的诱导下要求被告永信公司生产的,既不能说明被告永信公司以前生产销售过案涉侵权产品,也不能说明被告赵树亮之前销售过案涉侵权产品,涉案被告不存在侵权故意,相关行为亦不构成侵权,各被告不承担责任。在二审诉讼程序中,二审法院基于原被告的磋商购买聊天记录,认定原告的代理人仅是询问被告赵树亮是否有涉案包装的产品,并不存在提供包装进行定制或者诱导其出售涉案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被告关于涉案被诉侵权产品系“陷阱取证”行为的主张没有证据支持。尽管该案中二审法院并未对机会提供型以及犯意形成型进行详细的阐述,但是一二审迥异的判决结果已经可以看出法院在类似问题上的态度,即在不存在提供包装进行定制或者诱导被告出售涉案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的情况下,“陷阱取证”获得的证据合法有效。
而在专利领域,法院更是明确在判决中对“陷阱取证”进行了分析,并对机会提供型的取证进行了详细论述。在北京凯来美公司诉天津泰达低碳公司侵犯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一案中,被告泰达低碳公司认为原告凯来美公司主动向其发出购买侵权产品的邀约,属于设立陷阱收集证据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明确,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以设立陷阱的方式取得的证据,应当区分情形予以判断。若未对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即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据被采纳。泰达低碳公司若无销售意图,可以对购买邀约不予回应,况且,也无证据表明泰达低碳公司的销售意图源于凯来美公司。因此,凯来美公司所发出的购买邀约仅是向泰达低碳公司提供了一个销售机会,意在使泰达低碳公司的销售行为暴露出来。凯来美公司的取证行为未超过合理的限度,也未对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因而其所收集的证据能够被采纳,可以认定泰达低碳公司存在销售侵权产品的行为。法院一审判决:泰达低碳公司立即停止制造、销售涉案侵权产品,并赔偿凯来美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费用人民币1万元(含合理支出费用)。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法律适用
基于上述分析,尽管“七条”的规定表面上看起来是排除了部分取证的证据效力,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正当维权的权利人来说,侵权取证的目的是为了固定已经发现的侵权事实,而不是为了侵权赔偿而故意诱使侵权人产生侵权故意进而实施“侵权”行为,该条规定与法律的价值导向是一致的。
此外,即使是在司法实践中,即便被控侵权人以该条规定为由,主张被控侵权人仅基于他人的取证而实施了侵权行为,因此权利人取证的证据应排除,按照《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侵权人所做的抗辩是一种“积极抗辩”,侵权人也应当对“仅基于他人的取证而实施了侵权行为”这一事实进行举证,而不是将该举证责任转移给权利人。
笔者认为,在现行民事诉讼实践中,如果被控侵权人希望举证“仅基于他人的取证而实施了侵权行为”,那么其必须举证“仅”,意味着被控侵权人需要对一段时期以来的相关销售情况、进货单据、销售单据等进行举证以说明从事被诉侵权行为系偶发且仅因他人的购买等诱导行为而为之。因为相关销售情况是由被控侵权人掌握的,举证责任由侵权人承担也是当然的要求。如果其无法举证,即需要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在《知识产权证据规则》施行后,司法实践中,亦有被告在商标侵权诉讼中援引该条进行抗辩,主张并不侵害原告的商标权。在该案中原告关于侵权行为的举证即为现场购买侵权商品的公证书。,在被告未提交“仅基于他人的取证而实施了侵权行为”证据的情况下,法院未对被告的抗辩予以采信,亦并未要求原告进一步举证,而是基于原告的取证证据判令被告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
综上可知,《知识产权证据规则》的规定,对于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的权利人来讲,首先是在立法层面对取证的方式及取证效力进行了规定,一改以往规定的模糊状态,使得商标权人以及专利权人的取证行为“有法可依”。从司法实践层面来看,相关规定并不会加大权利人的举证难度,而且能够通过制度设计建立诚信、公平的价值导向,符合市场环境中正当权利人与其他市场参与主体的利益,有助于提升知识产权权利人维护自身权利的可预期性,有利于对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的遏制与打击。
京ICP备05019364号-1 ![]() 京公网安备110105011258
京公网安备110105011258
近日,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本所”)发现,网络上存在将一家名为“广州海问睿律咨询顾问有限公司”的主体与本所进行不当关联的大量不实信息,导致社会公众产生混淆与误解,也对本所的声誉及正常执业活动造成不良影响。
本所特此澄清,本所与“广州海问睿律咨询顾问有限公司”(成立于2025年11月)不存在任何隶属、投资、关联、合作、授权或品牌许可关系,亦从未授权任何主体以“海问”的名义提供法律咨询服务,该公司的任何行为与本所无关。更多详情,请点击左下方按钮查看。